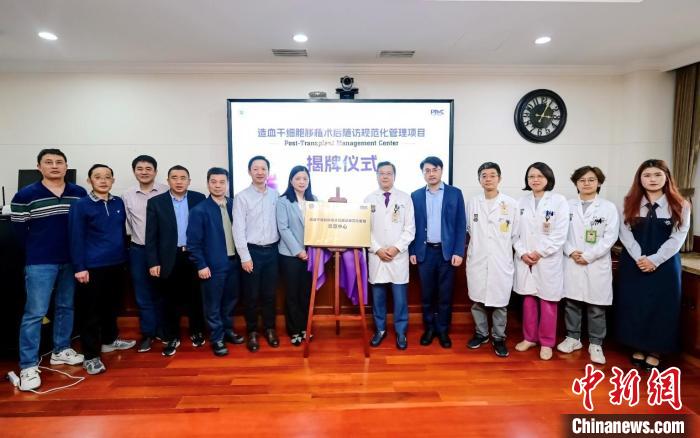叶嘉莹:西方文论与中国词学
老师的期许和我的经历
对词之美感特质的探索是我多年来所致力的一件事情,说到此一动念之开始,可能要推原到1945年,当时我大学毕业不久,我的老师曾给我写过一封信,其中有一段说:
……假使苦水有法可传,则截至今日,凡所有法,足下已尽得之。此语在不佞为非夸,而对足下亦非过誉。不佞之望于足下者,在于不佞法外,别有开发,能自建树,成为南岳下之马祖;而不愿足下成为孔门之曾参也。然而“欲达到此目的”,则除取径于蟹行文字外,无他途也。……(顾随1946.7.13致叶嘉莹书信)
我的老师名字是顾随,顾随拼成英文念起来像“苦水”,所以他自称是“苦水”,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句话是,“然而‘欲达到此目的’,则除取径于蟹行文字外,无他途也”。意思是说真的要想在老师说法的道理以外“别有开发,能自建树”,是要把英文学好,取径于西方的学问。我的老师这样写了,但其实当时我的英文并不是很好,因为我生在一个乱离的年代,当我读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发生了卢沟桥事变,日本占领了北京以后,我们增加了日文课,英文课被减少了很多。我大学读的是中文系,也没有好好地学英文。毕业以后不久,1948年 3 月我就结了婚,我先生当时在海军工作,所以我就离开了北京到了南京,可是不久,就在那一年的十一月,国民党的海军从南京撤退了,我就跟随我的先生一起从南京经过上海坐船来到了台湾左营的海军军区,当时左营的军区刚刚建成,一片荒凉。
曾在我们家外院南房住过的许世瑛先生当时也在台湾,他就介绍给我一个在彰化女中教书的工作。在彰化女中教书的第二年暑假,我生了一个女儿,我女儿三个多月大的时候,我先生就因匪谍嫌疑被捕入狱了。第二年暑假,我们彰化女中的校长和六个教师,包括我带着吃奶的女儿,都被抓进了彰化警察局,而且要把我们送到台北宪兵司令部。我抱着我的女儿去找了警察局长,说我在台北无亲无故,万一我有什么事,我的女儿连一个可以托付的人都没有,这个警察局长还不错,就把我放出来了。放出来后我无家可归,就只好去左营投奔我先生的姐姐、姐夫。我去到左营,一方面是投奔亲戚,一方面也想在左营可以打听我先生的消息,因为我先生就被关在左营。当时我们居住的环境都很窄,他姐姐、姐夫一间卧室,她婆婆带两个孩子一间卧室,我没有地方可住,只有每天等他们大家都安睡以后,才能在走廊上铺一个毯子带着我吃奶的女儿打地铺。暑假以后,幸而有人介绍我到台南一个私立女中教书,暂时有了一个安身的所在。三年以后,我先生被放出来了,证明我们没有问题,我才找了台北的一个工作,当时许世瑛先生在台湾大学教书,听说我们从台南来到台北了,马上就介绍我到台大去教书了。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学什么“蟹行文字”,可是天下有很多事情,有时候我真的觉得上天带领一个人是非常奇妙的,我先是在台大教书,后来台湾成立了淡江大学,许先生做中文系主任,就邀我到淡江去兼课;辅仁大学在台湾复校了,当年辅仁大学教过我的老师戴君仁先生做了系主任,也邀我去兼课,所以我就教了三所大学,而且都是专任,还教了一个教育部的大学国文广播课程、一个教育电视台的古诗课程。当时我们中国大陆对外不开放,所以西方很多研究汉学的学者就都到台湾去交流。这时台大的钱思亮校长通知我,说已经答应了密歇根州立大学把我交换出去,要我补习英文。当时来面试的学者是哈佛大学的海陶玮教授,海教授面试以后就要求把我交换到哈佛,请台大另外派一个人到密歇根,但台大的钱校长说已经答应了密歇根,不可以换人。海教授就要求我七月先到哈佛,九月开学再到密歇根。我在密歇根交换了一年,第二年哈佛大学就邀请我去做访问教授。南开大学出版过上下两册《中英参照迦陵诗词论稿》,是中英对照的我的论文集,就是哈佛大学的海陶玮教授邀我去合作时,我帮他翻译陶渊明的诗,而他就把我很多篇文章都翻译成了英文,海陶玮先生本来是学中文的,他应该跟我用中文对话,可是他跟我讨论的时候总是说英文,所以我就学了很多关于中国诗词的英文术语。
这个时候我已经把我先生跟女儿接出去了,其实主要是我先生一心要出去,而且出去以后就不肯回台湾了。可是我的交换期是两年,两年期满我坚持要回台湾,因为台湾三所大学的中文系负责人,台静农先生、许世瑛先生、戴君仁先生都对我非常好,现在人家开学了,我不能不回去,不能做这样对不起人的事情,何况我还有80岁的老父亲在台湾,我就回台湾去了。回去以后我要把我父亲接出去,但是我并没有能回到哈佛,因为美国说你除非办理移民,否则不能接我父亲出来,所以我过不去美国,海陶玮先生就又把我介绍到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去教书。我为了养家糊口在那里教书,可是作为一个专职的教授,我不能只指导两个研究生,学校说我要教大班的本科生的课,所以我就被逼地要用英文讲课,还要用英文看学生写的论文,所以我的英文就慢慢被逼出来了。而且我这个人不但是好为人师,同时也好为人弟子,我就抽了空去旁听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英文诗的课程和英文文学理论的课程,那个时候我没有想到我学这些英文、听这些课程有什么作用。是到若干年以后我才明白,我老师说的“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取径于蟹行文字”的重要性。
西方文论与中国词学
下面我要说到我平生所致力研究的一个问题,就是“西方文论与中国词学”,这不是一个现成的题目,我不是用一个西方的词语或理论来套在我们中国的文学上。以前有些人这样做,比如他说外国的文学很多词语都有一种象征的意思,他就说中国诗里边常常说香炉、蜡烛,应该也有象征的作用,香炉就是女性的象征,蜡烛就是男性的象征,可是我们中国诗歌从来没有这样的传统,“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杜牧《赠别》),并不是男性女性的象征。他们的说法是生搬硬套,而我用西方文论解释中国词学,是我几十年慢慢研究出来的结果。因为中国的词学始终没有建立起来。直到张惠言、王国维也没有建立起来。大家都恍兮惚兮,觉得词里边是有些个诗所未曾表达出来的东西,我们普通说诗词,好像都是韵文,都是抒情写景之作,其实“诗”与“词”两种文类是有着非常大的根本的差别的。
首先,从杜甫的几首诗看诗之言志的特质。诗的根本的作用是言志,“诗言志”的说法是从《尚书·尧典》就开始的,“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把你内心的“志”用言语表达出来,这就是“诗”。杜甫是正宗的诗人,是中国诗歌言志传统的代表,所以读杜甫诗是学诗的基础,读诗一定要从杜甫入手。杜甫写过《自京窜至凤翔喜达行在所三首》,写的是自己从沦陷的长安逃到肃宗行在之凤翔的过程,是自己血泪经历的诗篇,这是真正的好诗。判断一首诗是不是好诗,第一,要看其所写的是不是与自己生命生活密切相关的、发自内心的情志;第二,是有了这种生活的体验,有了真挚的感情,你怎么样表达。所以是要能感之,而且能写之,这是杜甫之所以了不起的地方。下面我们就举引他的《喜达行在所》三首诗中的前两首来看:
其一
西忆岐阳信,无人遂却回。
眼穿当落日,心死着寒灰。
雾树行相引,连山望忽开。
所亲惊老瘦,辛苦贼中来。
他先从自己对祖国后方的怀念写起,“西忆岐阳”,岐阳就是凤翔,在长安的西北,没有一个人从后方回来能够把大后方的信息告诉他,所以“西忆岐阳信,无人遂却回”。“眼穿当落日”,我每天向西方看,望眼欲穿,“心死着寒灰”,心断念绝,所以他忍不住才从长安逃到凤翔去。这是杜甫写的三首诗中的第一首,像我们八年抗日,当时我们沦陷在北平,真是不知道我们的国家政府什么时候回来,我的父亲什么时候回来,我的母亲去世了我的父亲现在在哪里,都不知道,这是我自己个人的亲身经历,所以对杜甫这类诗,特别有共鸣。
其二
愁思胡笳夕,凄凉汉苑春。
生还今日事,间道暂时人。
司隶章初睹,南阳气已新。
喜心翻倒极,呜咽泪沾巾。
我说过,一个人要能感之而且能写之,你内心麻木不仁,什么都没有感觉,当然写不出诗;你心里有感觉、有感情,而不能够恰到好处地把它说出来,也不成诗。可是作诗其实没有什么困难,每个人的内心都有感受,把自己内心的感动写出来,这是每个人应该有的权利。杜甫写得真是好,“生还今日事,间道暂时人”,我今天还活着,我真的回到后方见到我的朋友,我才知道我是活着回来的,可是当我在“间道”,就是小路上偷偷地逃跑的时候,我是“暂时人”,因为我不知道下一刻、下一分钟我会碰到什么,我不知道还能不能活下去。
杜甫的诗真是血泪写成的,他还写过一首题目很长的诗,《至德二载甫自京金光门出间道归凤翔干元初从左拾遗移华州掾与亲故别因出此门有悲往事》,杜甫投奔到后方,后来肃宗收复了长安,杜甫做了左拾遗,他跟着皇帝回到长安,心里高兴得不得了,这是他平生的志意,要为朝廷做一番事业,看到朝廷的缺失一定要提出谏言,所以他左上一篇奏疏、右上一篇奏疏,今天说你这里不对,明天说你那里不对,皇帝一生气就把他贬出去了。杜甫因此有很深的悲慨,我当年是从这个金光门九死一生地逃出去投奔了我的祖国,现在朝廷把我给赶出去了,我走的就是我当年投奔它时所走的那个门,所以他说“因出此门”,我又走了这个门,“有悲往事”:
此道昔归顺,西郊胡正繁。
至今犹破胆,应有未招魂。
近侍归京邑,移官岂至尊。
无才日衰老,驻马望千门。
第一句他说“此道昔归顺”,我就是走这条路投奔的祖国,“西郊胡正繁”,那时候长安城的西郊都是胡人,都是安禄山他们的兵马,我可能随时被抓,随时被杀死。“至今犹破胆,应有未招魂”,我当年真是心惊胆破地逃出来,我到现在还惊魂未定。“近侍归京邑”,我以亲近皇帝左右的左拾遗的身份返回长安,“移官岂至尊”,现在把我赶走,这难道就是皇帝的意思吗?“无才日衰老,驻马望千门”,我现在要离开我真正关心的国家首都所在的长安,我无才而又衰老,我还能够回来吗?我不忍离开,所以我就停下马来“望千门”,“千门”指的就是都城的宫殿。杜甫从此一去,再也没有能够回来,只能“每依北斗望京华”(《秋兴八首(其二)》)了,最后死在道路之上。我们看杜甫的《干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这一组诗是写他从秦州到成都去,经过同谷的时候,天寒、冰雪载途,没有食物吃,杜甫到山上去挖植物的根,他说“长镵长镵白木柄,我生托子以为命”,我现在靠这个铲子活命,可是我铲了一天,没有挖到任何可以吃的食物。杜甫真是历经艰苦,他的诗真的是言志的诗篇,所以杜甫是诗里边的诗圣,而且是正宗。我也喜欢李商隐,可是李商隐的诗绝不是正宗。我们现在说的是诗,后来出现了词,词跟诗是完全不一样的。
其次,再谈词之源起与《花间集》对后世之影响。中国文化曾有几次的进展和转化,都受有外来文化刺激的影响,如果没有外来文化刺激,而是陈陈相因,文化就越来越衰微了。我们知道词最早就是敦煌曲子词,敦煌曲子的产生是因为西域的胡乐传到中国来了,敦煌是个交通的要道,所以传到敦煌,当然它也不完全是新来的,它是把西域的胡乐,跟中国宗教的法曲,与原来的清乐结合起来的一种新的音乐。是因为有外来的因缘,才有了敦煌的曲子。敦煌的曲子是新的音乐,有很多新的调子很好听,就有许多人给这些曲调填写歌词,可是当时来往的主要是商人,文化水平不是很高,所以敦煌的曲子文字都不够典雅,直白浅露,而且还有错字、别字。可是后来有些文人听到这些曲子,就也按照这新的调子填写一些歌词,像白居易就写过《忆江南》。填写歌词的诗人文士慢慢多了,所以后来到了五代的后蜀,赵崇祚就编订了一册《花间集》,欧阳炯为这个集子写的序文说编辑《花间集》的目的、动机就是“庶使西园英哲,用资羽盖之欢;南国婵娟,休唱莲舟之引”,要给那些美丽的歌儿酒女编一本歌词的集子,让她们唱一些文人写的美丽的歌词,不要只唱那些庸俗的调子。所以《花间集》本来是搜集了诗人文士所作的一些比较文雅的歌词,给那些歌儿酒女在歌筵酒席之间歌唱的歌本。我们只看《花间集》的名字,表面就是一个书名,其实它的取义在花丛里边唱的歌,花丛里边唱的歌写什么,主要就是美女跟爱情。所以《花间集》中所收的歌曲都没有题目,只有曲调的名字,这与杜甫那一类所谓言志的诗,实在有很大的不同。但有的时候,世界上一个偶然的事件,有可能会对后来产生极大的影响,西方称之为“蝴蝶效应”,说南美洲森林里面一只蝴蝶扇一扇翅膀,结果大洋彼岸就可以引起一场风暴,这当然是夸张的说法,就是有时候一件小事情,结果在世界上发生了重大的影响。我以为《花间集》的出现在文学史中、在诗歌方面就有这种蝴蝶效应,它使中国的小词有了这么深厚的意蕴,成了一种足以跟诗对立的文体,它的分量、内容、情意可以跟诗站在平等的地位,而它能够写出来诗所不能够写出来的东西,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
后来的读者从小词里面看到了很多很多的意思,但它在表面上都是写美女跟爱情,可是它可以引起读者很丰富的联想,这是为什么呢?这些联想又是何所指向呢?温飞卿的《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表面所写的就是一个女子早上起床、化妆、换衣服这样的情景,用中国传统的说法从内涵说起来,温庭筠所写的就是闺怨之词,就是写一个孤独的女子。“小山重叠金明灭”,太阳出来了照在屏风上,有闪烁的光影,“鬓云欲度香腮雪”,这个女子一转头,头发从脸上遮过来了,然后她起来了,“懒起画蛾眉”,而屈原《离骚》曾说“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唐朝杜荀鹤《春宫怨》也曾说“早被婵娟误,欲妆临镜慵。承恩不在貌,教妾若为容”,中国传统诗歌里边所写的女子就是宫怨和闺怨,所以一般中国的女子都是思妇、怨妇。而在中国的诗歌里为什么都是思妇、怨妇呢?从《古诗十九首》“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就是如此,这是中国的社会伦理的家庭制度所形成的必然的结果,“好男儿志在四方,岂能株守家园,效儿女子之态”,男人是一定要出去,不管你是在文治武功上建功立业,还是行商坐贾,“前月浮梁买茶去”,男人为了谋生,他必须出去,而女人则是一定不可以出去,一定要闭守在家门之中侍奉翁姑、教养子女、料理家事。整个历史的社会的背景就注定了中国诗里面的女人都是思妇、怨妇。男人出去了,女子在家中那当然就是思妇,一天到晚相思怀念,不知道丈夫哪天才回来,“门前送行迹,一一生绿苔”“八月蝴蝶黄,双飞西园草。感此伤妾心,坐愁红颜老”(李白《长干行》),这是思妇。如果这个男子在外边另外跟别的女子好了,甚至于结了婚,家中的女子就从思妇变成怨妇了,《西厢记》里边崔莺莺就对张生说“若见了那异乡花草,再休似此处栖迟”。温庭筠这首词就是写一个女子化妆、爱美、要好,最后“新贴绣罗襦”,衣服上最近贴绣的罗襦的短袄,绣的是“双双金鹧鸪”,这就跟一对鸳鸯的象征是一样的,是用来反衬女子的孤独寂寞。
张惠言以比兴寄托论词,说温庭筠的词是“感士不遇也。篇法仿佛长门赋,而用节节逆叙”(《词选》)。但是温庭筠写的这个美女,很可能就只是写一个女子因所爱的人不在家的那种寂寞的情怀,有什么贤人君子的用心?所以王国维就反对张惠言,他说“飞卿《菩萨蛮》……兴到之作,有何命意?皆被皋文深文罗织”(《人间词话》)。于是王国维就想自己为词的特质下一个定义,说“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他说词里有境界,可是王国维也没说明白境界是什么,而且王国维从一开始就混乱了,他说的是词里有境界,可是他后边所举的例证,说“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优劣。‘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何遽不若‘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都是诗的例证。我初中一年级时,母亲给我买了一套《词学小丛书》,我就读了词,也读了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我觉得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有几段写得好,就是他评温韦冯李四家词,可是他所说的境界,我从小就没有看明白。大家都觉得词很微妙,可以给读者很多联想的可能,可是你说它是什么?是比兴寄托,太狭窄了;是境界,太广泛了,张惠言、王国维他们都没有把词真正的好处和作用说明白。
小词里面有一个可以引起读者非常丰富的,而没有一定专指的种种的联想的作用。那么这个东西应该叫什么,而且这种作用是从何而来的?这是中国文学史上从来没有回答、没有解决,从来没有人真正解说明白的一个问题,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直到我去了北美,看了很多西方的理论,才慢慢能够说明。不是说西方的理论就比中国的好,但西方的理论是思辨性的,不像中国的诗词评论只是印象的描述,而且我去到北美的那个年代是西方的文学理论最盛行的一个时代——20世纪60年代,我是1966年出去的,1967、1968年在美国,回到台湾一年,1969年去到加拿大。很多新的理论,而且是非常好的、精华的、扼要的理论都是那个时候出现的,其实现在西方的文学理论已经没有那么精彩了,已经走入一条驳杂而不是很正常的道路去了。我赶上了那个时代,也看了很多西方理论的书,同时因为我要用英文教书,“境界”跟“兴趣”说不明白的,我就尝试用了西方的理论来解说。
再次,从女性主义理论看《花间集》与传统诗歌中女性叙写之不同。上个世纪中期正是女性主义盛行的时候,女性主义兴起之初的旨意本是要追求男女平权,法国女性学者西蒙·德·波伏娃写过一本书,《第二性》。西蒙·德·波伏娃讲男女平权的书与小词有什么关系呢?因为《花间集》都是写美女跟爱情的,不管是用男子的眼光或者是用女子的口吻写,要研讨词的特质一定要重视《花间集》中的女性叙写,所以要从女性主义谈起。西蒙·德·波伏娃的《第二性》提出女性是第二性,是男性眼中的“他者”,是“被男性所观看的”对象。而且她说男性看女性是带着男子的性趣味的这样的一种凝视,这是西蒙·德·波伏娃站在男女平权的这种思想上所提出来的。我们回到《花间集》,看看中国早期《花间》词中所写的几种女性形象。
第一种就是西蒙·德·波伏娃所说的被男性作为观赏对象的女性,像欧阳炯的《南乡子》:
二八花钿,胸前如雪脸如莲。耳坠金环穿瑟瑟,霞衣窄。笑倚江头招远客。
“二八花钿”,二八一十六,女子最美丽的年华,这个女孩子头上戴着花钿,“胸前如雪脸如莲”,这是男性的眼光看到的,“耳坠金环穿瑟瑟”,耳朵上戴着黄金的耳环,上面还穿有“瑟瑟”的颜色美丽的珠饰,“霞衣窄”,穿着很窄的紧身的彩霞一样的衣服,“笑倚江头招远客”,一个摆渡船的女子含着微笑在江边招呼客人来上渡船。这是《花间集》里边写的男人眼中的女性。
第二种就是爱的对象,像欧阳炯的《浣溪沙》,完全是爱欲的描写:
相见休言有泪珠,酒阑重得叙欢娱,凤屏鸳枕宿金铺。兰麝细香闻喘息,绮罗纤缕见肌肤,此时还恨薄情无。
以上是《花间集》中的两种女性形象,是从男性的眼光来描写女性。可是《花间集》中的歌词是要交给歌儿酒女去唱的,所以它也有用女性的口吻来写的,那些用女性口吻写的词又是怎样的呢?
《花间集》中第三种女性的形象就是独处之女性的相思期待,像温庭筠的《菩萨蛮》:
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
不要轻易地被张惠言用屈原的《离骚》绑架过去,客观上,这首词所写的是一个独处的寂寞女性早晨从她被日光惊醒到起来描眉化妆穿衣照镜的过程,是一个思妇的形象。至于你因为他说蛾眉而想到屈原,那是张惠言的联想,温庭筠所写的是思妇、怨妇的形象。
所以《花间集》所写的三种女性形象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用男性的口吻来写的;另一类是从女性口吻所写的思妇、怨妇。那么《花间集》写思妇和怨妇为什么就会引起张惠言和王国维这么丰富的联想,总觉得它里边有些东西,为什么会如此呢?
诗里边也写这种孤独寂寞的女子,也是怨妇,可是词里边所写的怨妇就和诗里边所写的怨妇有了很大的差别。中国诗里边所写的怨妇大多是有家庭归属的,是具有家庭伦理的身份的。可是《花间集》里边那些个女性都是歌儿酒女,她没有家庭的归属,不是妻子、不是女儿、不是母亲,是无所归属的女性。西方女性主义的理论家也讲了各种的女性,1980年玛丽·安·佛格森编有《文学中的女性形象》一书,分女性形象为五种类型,有妻子、母亲、偶像、性对象及没有男人的女性。这是西方的女性主义归纳出来的西方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西方没有词,他们归纳这些形象的根据是西方的小说。
卡罗琳·郝贝兰就提出女性不只是这样的形象,有的女性的作者或者有的男性的作者是双性人格的。双性人格本来指医学上的雌雄同体,或者是身体上的双性同体,或者是心理上是双性同体。卡罗琳·郝贝兰的《朝向雌雄同体的认识》一书讨论的则是文学上的双性同体。
美国学者劳伦斯·利普金是一位跟我同时代的理论家,我在哈佛大学教书时,他在西北大学教书。利普金写过一本书《弃妇与诗歌传统》。他说弃妇的形象是一个诗学传统,古今东西都是如此,而且写弃妇的作者往往是男性。男子有时不被重用,甚至被同事所轻视,也常常有被抛弃的感觉,而且男人比女人更需要弃妇的形象。如果一个女子被抛弃,“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古诗十九首·青青河畔草》),“前月浮梁买茶去”(白居易《琵琶行》),她可以直接说出来;可是男子更要面子,他在外边如果不得意,是不肯说的。所以利普金说其实男子更需要这种被弃的形象。中国的小词表面上所写的是一个弃妇,可是很多被弃的男性就把自己套进去,而且他不但是读别人的弃妇形象有很深的感受,他自己也写弃妇,也许表面上他的显意识里边写的是弃妇,可是他的潜意识之中,其实是表达了他自己失意的感情。所以小词里边所写的弃妇就很可能有男子的托喻,所以张惠言说温庭筠的“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是“感士不遇也”,这是一个男子得不到他人的欣赏,不被人家重用,所以他写了一个寂寞的女子的形象。《花间集》里的女性形象可以引起男子这么丰富的联想,不管他是把这个女子作为爱情所投注的对象,还是下意识地把自己在仕宦上的不得志代入女子的相思怨别之中。我们现在是从女性主义来看小词的微妙,从基本的理论说明小词为什么可以引起人这样丰富的联想、可以被人解成有很多寄托、很多隐喻。这不是我抄袭的,这些零零碎碎的理论都是我多年来,自己一步一步看书、读书、思考建立起来的。
第四,从诠释学与接受美学看小词的微妙作用。我们用女性主义说明了为什么词的女性叙写给读者丰富的联想,下一步我们要谈的就是这些联想该怎么样解释?所以我们就要从女性主义过渡到诠释学的理论。诠释是我们所需要的,一首诗要诠释,一篇文章也要诠释,一首词更要诠释,但是如果按照诠释学的理论来说,我们却永远找不到主体的原意。每一个诠释的人其实都是带着他主观的背景,他的性情、爱好、学识、经历,所以你看这首小词看出这么多意思来,他看这首小词看出那么多意思来,要找到作者原来的意思是什么,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一种诠释都来自诠释者自身的主体意识,这是一个循环,西方的诠释学有一个术语就是诠释的循环。威廉·燕卜荪有一本书《多义七式》,其中说道诗歌的解释有时候是模棱两可的,他列举了七种模糊不清的、模棱两可的类型。解释一首诗、解释一首词不是那么简单、容易的事情,你不知道这是不是作者的意思,而且它有多种解释的可能。“感时花溅泪”(杜甫《春望》),花上溅上了我的泪点吗?花瓣落下来像花在哭泣吗?所以诠释的循环,你就代表诠释者自己,而且它有这么多模棱两可的可能性。诗还比较容易解释,因为诗是显意识的言语,可是小词就是写的美女跟爱情,这个作者写这个美女跟爱情的时候,他的显意识或他的潜意识里边是怎么来写的呢?同样写水边的女子,欧阳炯说“二八花钿,胸前如雪脸如莲”(《南乡子》),薛昭蕴说“越女淘金春水上,步摇云鬓佩鸣珰,渚风江草又清香”(《浣溪沙》),欧阳修说“越女采莲秋水畔。窄袖轻罗,暗露双金钏。照影摘花花似面。芳心只共丝争乱”(《蝶恋花》),同样是美丽的女子,同样穿着美丽的衣服,为什么不一样呢?欧阳炯的容易懂,可是欧阳修到底要说什么呢,“照影摘花花似面”,芳心为什么 “只共丝争乱”,是什么使她的心乱?小词有的时候就在写美女之中有一种很微妙的东西,可以引起读者很丰富的联想,而它不是一个显意识的,它是隐意识的,是一种不知不觉的流露。
不管是中国的文学批评还是西方的文学批评,最初都是重视作者,作者写这首诗是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写给什么人,要考证一番。后来随着时代的演进,西方文学批评的重点转移了,从作者转移到了作品,我们说杜甫缠绵忠爱不是说杜甫这个人缠绵忠爱,是他的作品使我们感到缠绵忠爱,使我们感动,不能因为作者是好人就说作品是一首好诗,而是因为诗的语言文字使它成为一首好诗的。于是就出现了新批评,脱离作者来到作品,诗的好坏在作品不在作者。T. S. 艾略特提出细读,要一个字一个字地去读,这两个字的结合有什么样的作用。西方的文学批评有几次演变,从作者到作品,从考证到诠释,诠释的依据是符号,他为什么说“美女”不说“佳人”,说“红粉”不说“红妆”,符号是重要的,所以要细读,重视每一个符号的作用。于是西方文论就有了符号学,要以作品为主,以符号为主。你说因为杜甫是忠爱缠绵,所以他的诗就是好诗,这是意图谬误说,意图好不见得写出好的作品来,要重视的是作品本身的符号的表现。还有就是感应谬误说,有人说这首诗写得太好了,我一边看一边流泪,这就代表着这是一首好诗吗?诗自有它艺术的价值,不是说让你哭了就是好诗。
后来批评的重点又转移到读者,捷克结构主义批评家莫卡洛夫斯基,在《结构、符号与功能》一书中,将一切艺术作品分为两种,一种是艺术成品,另一种是美学客体。如果单独的只是一篇作品的话,它是一个艺术成品,比如杜甫的诗是一个艺术成品,你给不懂诗的人去看,它丝毫不起作用,所以诗是什么呢?诗是当这个作品被读者读到的时候它才成为一个美学客体,才有了美学的作用,真正把这个作品的价值完成的是读者,如果没有经过读者的阅读,杜甫的诗摆在那里再好它也只是一个艺术成品而不是一个美学客体。所以批评的重点从作者到文本,到读者,读者的接受,读者怎么接受。
德国的沃夫冈·伊赛尔就提到接受的美学,他有一篇很重要的文章《阅读活动——一个美学反应的理论》,他说阅读的时候有两个极点,一边是作者,一边是读者,中间是文本,所以从作者到作品到读者都是重要的,缺一不可。没有经过阅读就只是一个艺术成品,阅读以后它才成为一个美学的客体。杜甫的诗再好,“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杜甫《秋兴八首·其二》),你给一个不懂诗的人去看,他根本不知道这说些什么。所以真正把作品完成,使它有价值、有意义、成为一个美学客体的是读者。按照西方的接受美学来说,读者对于小词可以产生这么多的联想,是因为小词里边有一种“ 潜能”,就是潜藏在小词里边的一种能力,你为什么觉得这个作品好,为什么觉得这个作品给你丰富的联想,是因为它的文本,文字的本身给作品一种潜在的可能的潜力。
第五,我想谈谈创造性背离与小词蕴藏的潜能。我努力了这么多年,很想把小词的微妙的作用找寻出来并加以说明。词的特色不要说那是比兴寄托,这是牵强附会;也不能说那是境界,这太浮泛了,都是不可靠的。我说好的词包含了丰富的潜能,词作品的本身包含了许多潜能,而这个作用要读者来完成,是张惠言说蛾眉有屈原《离骚》的托意、是王国维从词里面读出来有成大事业大学问的三种境界,这都是读者在接受的时候提出来的,而作品的本身提供的是一种潜能。
现在我要提出来一个更进一步的理论,我很欣赏一位意大利批评家弗兰哥·墨尔加利,他写了一篇文章《论文学接受,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创造性背离的说法,这就给了作品的内涵更多更丰富的可能性,当你读它的时候,你所体会到的可以不是作者的原意,你在接受的时候,可以有创造性的背离。
最近大陆要出一本我在温哥华曾经出过的书,是我的一些诗词的英文翻译,这本书完全是温哥华的翻译家陶永强翻译出版的,他给这本书起了一个名字叫《独陪明月看荷花》。我想陶先生之所以选这个名字,是因为他知道我的小名叫小荷,因为我是在荷花的月份出生的。那这“独陪明月看荷花”是从哪来的呢?这是我的梦中得句,孔子说自己老去了,“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我现在是“久矣不复梦中得句”。我以前会在梦里出现一些诗,有的时候是一句,有的时候是两句,有的时候是一副联语,我觉得梦里出现的断句很有意思。“独陪明月看荷花”是我梦到的一句诗句,我醒来以后想把它凑成一首诗,可是我怎么凑都凑不成功,因为人的显意识的活动跟潜意识的活动是不一致的,我怎么说都觉得被限制了、被拘束了,它本来是活的,你一说明就给它套圈子,它就死了。我平时很喜欢李商隐的诗,自己凑不成功,就忽然想到拿李商隐的诗拼凑了一首七言绝句(《梦中得句杂用义山诗足成绝句一首》):
一春梦雨常飘瓦,万古贞魂倚暮霞。
昨夜西池凉露满,独陪明月看荷花。
前三句都出自李商隐的诗,“梦雨”句,是《重过圣女祠》一诗的首句;“贞魂”句,是《青陵台》一诗的第二句;“昨夜”句,是《昨夜》一诗的第三句。我这里完全脱离了李商隐原来的诗意,李商隐的《重过圣女祠》是写传说中神仙一样的女子所住的地方是“一春梦雨常飘瓦”,他写的是雨中的圣女祠的景象,我把它断章取义拿过来了,对的是《青陵台》一诗的“万古贞魂倚暮霞”。“一春梦雨常飘瓦”,我所取的象喻是一种幽微隐约而飘忽不定的情思;“万古贞魂倚暮霞”,我所取的是一种上冲霄汉的光影,象喻的是坚贞的品节和持守,这两句都是抽象的景象。至于李商隐《昨夜》一诗,全诗是:
不辞鶗鴂妒年芳,但惜流尘暗烛房。
昨夜西池凉露满,桂花吹断月中香。
首句出于《楚辞》“恐鹈鴂之先鸣兮,使夫百草为之不芳”,当鹈鴂鸟一叫的时候春天就过去了,本来我们都害怕鹈鴂一叫春天就走了,可李商隐说“不辞”,对于这种春天的消逝,我不逃避也不推辞,我的悲哀不在春天的不能挽留,我所惋惜的是“流尘暗烛房”,蜡烛的烛心应该是最光明的,代表一个人心头的光焰的闪烁,可是我这点内心的光明被尘土给遮暗了,这是最值得惋惜的。“昨夜西池凉露满”,西方属金,是肃杀的,那么寒冷、凄凉、肃杀的西池,而且是满池的寒露,在这样心断望绝的寒冷的环境之下,古人传说天上的月亮里边有桂花树,八月十五月圆之日,天上的月亮会飘下桂子落在地上,“桂花吹断月中香”是说我那美好的希望和想象已经完全断绝了。我说“一春梦雨常飘瓦”是情思的绵渺,“万古贞魂倚暮霞”是持守的坚贞,“昨夜西池凉露满”,在这样寒冷的环境下,我把我的那句“独陪明月看荷花”加上去,寒风冷露之中的荷花,映着天上的一轮明月。我用的是李商隐的意思吗,不是啊,所以我们用古人的句子,我们的解释可以违背它的愿意,把自己创造的情思放进去,就是文学接受中的创造性背离。我将李商隐的诗搬到这里来,是创造性的背离,王国维用成大事业大学问说晏殊、欧阳修的小词,也是一种创造性的背离。词这个东西是很微妙的,从作者到作品,到接受到诠释,甚至于你接受和诠释的时候可以不是作者的原意,这是小词的微妙的作用。我认为在中国的文学史中,《花间集》本来是歌筵酒席之间为歌女而编,可是它却在我们后来文学演进的历史上发展、达成了这么丰富这么微妙的启示和作用。而我们中国历代的学者曾经努力过,曾经尝试过要给它一个解释,张惠言说它是比兴寄托,王国维说它是境界,都不能使人信服。
对老师期许的回答
我既然喜欢词,我一辈子都在教词,我就要把这个问题解决,所以我引了中国的词学,也引了西方的各种文学理论,我要给中国小词的微妙的作用一个说法,我不能限制在比兴,不能漫无边际地说那是境界,我所提出来的是小词中有一种潜能,而这个潜能之所以形成,有我上边所说的这么多的原因。所以我一直认为,我一生之中真正努力完成的,是要把词的美感特质,它的缘由、作用、理论解说出来,这真正是我自己独立完成的对于词的特质的一个根本的诠释和说明。我以为这在词学领域是很重要的开拓,解决了词学的一大问题,同时对于我的老师给我的书信中所提出的要取径于“蟹形文字”的教导,也可以算是一篇读书报告吧。
(叶嘉莹系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感动中国2020年度人物”。本文由闫晓铮根据叶嘉莹在北京横山书院和在天津南开大学寓所两次所讲《西方文论与中国词学》的录音整理而成,经叶嘉莹审定授权本刊发表)
《博览群书》,1985年创刊,由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题写刊名,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撰写发刊词,是光明日报社主办的综合性思想文化月刊。“砥砺思想,宁静心灵”是我们的追求,“知识人写给知识人”、“名家作品名家看”,已被这本杂志坚守39年。
阅读剩余全文()